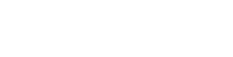2006年春,在成都郊外蓝顶艺术区,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组以“囚”命名的系列作品,由此而认识罗杰,一位语速平缓、气质温和,略显腼腆的艺术家。后来得知,罗杰当时刚刚进驻‘蓝顶’,拥有一间向往多年的工作室,其独特的个人创作风格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
相隔三年,我仍清晰记得初遇作品时的惊觫:肉身异化成粗砺纠缠的绳索,精神依然徘徊其中,咆哮冲撞,焦灼痛楚,又时有冷漠和凄惶。无论是危险不安的暴力场景,还是疏离疲惫的肢体语言,都令人困惑难解。又因似曾相识,更添遐想与恐惧。这种特殊而异样的视觉经验,从何而来?如果从发生学角度考量,图像生成乃是根植于个体的生命体验,那么,如何检索、唤醒及呈现潜伏的个人记忆,并把它转换成有意义的视觉表达,使其在当代社会文化情境中,具有特殊的符号学意义呢?基于此,我对罗杰的作品产生了兴趣。
罗杰就读四川美术学院期间,正值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中国当代艺术陷入沉潜期。此时,四川美院创作处境微妙:一方面,油画创作总体上与当代艺术并不相交,日益商业化的风情写实与日益主流化的乡土叙事相互助长,一度被港台画商所操纵。另一方面,四川美院当代艺术的个体探索并未停滞,并以其边缘、地下的方式持续进行。如张晓刚、叶永青、陈卫闽、杨述、张濒、忻海洲、郭晋等。更重要的是,从1991年开始,四川美院批评家王林逆流而行,策划组织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并发起对于“八九后艺术的讨论”,提出了包括“政治波普”在内的一系列艺术概念。这项活动延续十年历经六届,集中呈现了中国八九后艺术的创作倾向,并动员国内批评力量深入研究当代艺术问题与八九后中国美术现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以上三条线索,大致可以勾勒出罗杰当年身处的学习环境:沉闷、压抑,却不乏独立精神和批评锋芒。当然,还有学院门口不时辗过的坦克车,和新近生产的防暴车。这里靠近兵工厂,公路也是军械实验的道路。
这段时期,留给罗杰的生命记忆,对其后来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究其画面,至少有三点值得探源:
其一是其表现主义倾向。
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的表现主义创作倾向,汲取西方现代艺术成果转向直面本土社会及历史问题,寻求充满中国经验的话语表达。其价值在于,敢于直面当代人的心理矛盾、精神冲突及个体生命对生存异化的反抗。同时,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变化,揭示隐含其间的现实问题。至世纪之交,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精神面临着消费文化、权力资本和后殖民文化的侵袭,因利益共谋而将表现主义创作加以遮蔽。2006年前后,罗杰反其道而行之,其“囚”系列作品,深入内心揭示精神苦难,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个人曾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现实体验。这里有的是艺术良知和艺术家的尊严,而不是名利场逻辑。
其二是作品的象征性转喻。罗杰运用置换手法,让非物质的物质性与物质的非物质性之间产生歧义。其人物造型,并非鲜活的肌体,而是一具具用粗绳捆绕的活动模具,有着属人的表征却是被异化了的‘生物’。其作品把日常发生的情景进行陌生化处理,使之悬置于后工业化时代特有的冰冷时空中,从而让阅读者遭遇到文化、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象征性转喻不仅体现了画家强烈的个人情感,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批判性。同时,也是艺术家转换写实手法使之具有观念性的绘画方式。
其三是关于作品的个体化表达。如果说,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的相互开启是当代艺术创作存在个体化的基础,那么,罗杰的生活际遇则是其独特表现语言的诱因。罗杰毕业之后,迫于生活压力,独自南下谋生。结果可想而知。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物欲膨胀,就连空气也散发着铜臭味儿。每天高强度劳动过后,罗杰再也不想和这座城市发生任何关系,躲进书堆,寻找慰藉。正是这一时期,罗杰渐渐养成了文字书写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看似枯燥的工作,也令其颇有受益,即对绘画材料性能的熟练把握。工作中用的全是荷兰进口颜料和日本动画纸,这对罗杰而言,可是货真价实的奢侈品啊!但陌生的环境让他倍感孤独,甚至出现忧郁症倾向。1993年,罗杰怀揣两万块钱回到西南,还是想当艺术家!在重庆遇到了赵能智,封胜,何森,陈文波,杜侠等美院毕业的同学,后来又到了成都。一晃过了两年,罗杰花光了积蓄,无法支撑画画所需的基本开销,于是只能在成都杜甫草堂边上住下,画些小稿,生活毫无着落。画废了的纸张罗杰舍不得扔掉,用笔一遍遍地在上面重复勾勒涂抹。有一天,突然惊觉,这些线条怎么像父亲编织的渔网,这突如其来的记忆一下启发了他。
罗杰的父亲是一位孤独善良却脾气暴躁的男人,一生守护在青藏高原阿木柯河道班,是红原县318国道上的养路工人。为了远方妻儿补贴家用,经常编织渔网,捕鱼卖鱼。但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外出捕鱼,被一辆货车撞伤,再也不能站起来了。这位孤身流放的‘囚徒’因此回到家中。罗杰经常看到他坐在院子里,靠在椅子上编织着渔网。父亲离家日久,似乎忘了如何与家人交流,编织渔网是一种无需表达的生活方式,是其生命存在的唯一寄托与慰藉。自卑而又倔强的父亲,只有在编织渔网时,心灵才得以平静。那张永远也编织不完的鱼网,与父亲牵连了一生,深深嵌入罗杰的生命记忆中,成为其生命必须承受之重!
这样,一根线的无止无休的缠绕出现在罗杰的作品中,这就是他的作品“囚”系列。一方面,画面语言呈现于视觉充满了丑陋、毁灭与撕裂等负面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潜藏在罗杰内心深处强烈的修复欲望却不知不觉地被牵扯出来。父亲对爱的追寻,体现在对渔网周而复始的编织中,渔网对他而言,实用功能已退居其次。而罗杰在作品完成过程中,在编织纷繁复杂的绳索时,同样是在修复着无法忘却的伤痛。与父亲静态修复不同,罗杰属于动态修复,是艺术家把个体的经历与苦难,放置在一个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及共时性的空间背景中,思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反省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必须面对的文化制约,由此产生的批判精神。从2006年创作开始,“囚”系列作品从反抗激情和场景化的强烈冲突逐渐让位于个体化的复杂细腻的心理矛盾,如作品《敏感者》、《抽烟的人》、《哪里会是象牙塔》等。画面构成和人物刻画则愈见简练,看得出来,罗杰更倾向于敏感的体悟和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当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问题。
郑 娜
2009年4月11日
写于二沙岛广东美术馆
点赞 6 浏览 413
-
 《囚-都市守望者 》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 /2013
《囚-都市守望者 》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 /201394 x 68 cm | ¥ 12,000
3.2 -
 《囚-坠落 》 丝网版 /2013
《囚-坠落 》 丝网版 /201393 x 64 cm | ¥ 12,000
2.9 -
 《攀登高峰的人 》 数位版 /2013
《攀登高峰的人 》 数位版 /201350 x 50 cm | ¥ 6,800
2.9 -
 《囚-047 》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 /2021
《囚-047 》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 /202160 x 60 cm | ¥ 8,800
2.9 -
 《一块红布 》 数位版 /2013
《一块红布 》 数位版 /201350 x 60 cm | ¥ 6,800
2.8 -
 《囚-056》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
《囚-056》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47 x 60 cm | ¥ 8,800
2.3 -
 《囚-房地产商》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
《囚-房地产商》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47 x 60 cm | ¥ 8,800
2.3 -
 《Imprisoned- The moving cap》 综合材料/2015
《Imprisoned- The moving cap》 综合材料/2015180 x 210 cm | ¥ 378,000
2.2 -
 《囚-坠落》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
《囚-坠落》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60 x 50 cm | ¥ 8,800
2.2 -
 《囚-空间错位?行为错位?》 综合材料/2015
《囚-空间错位?行为错位?》 综合材料/2015150 x 180 cm | ¥ 270,000
2.1 -
 《囚-22》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
《囚-22》 德国哈里姆勒金属银钡纸/202147 x 60 cm | ¥ 8,800
2.1 -
 《囚-敏感者》 综合版画/2009
《囚-敏感者》 综合版画/200957 x 71 cm | ¥ 8,800
2.0 -
 《Imprisoned-hazy day -I》 综合材料/2015
《Imprisoned-hazy day -I》 综合材料/2015180 x 210 cm | ¥ 378,000
2.0 -
 《呐喊》 铸铜/2017
《呐喊》 铸铜/201740.5 x 70.5 x 45 cm | ¥ 210,000
2.0 -
 《囚-蓝布》 布面丙烯/2016
《囚-蓝布》 布面丙烯/2016150 x 120 cm | ¥ 180,000
2.0 -
 《囚—常规出行》 综合材料/2016
《囚—常规出行》 综合材料/2016150 x 150 cm | ¥ 225,000
2.0 -
 《囚-红布之十一》 布面丙烯/2015
《囚-红布之十一》 布面丙烯/2015100 x 120 cm | ¥ 120,000
1.9 -
 《囚-抽烟的人》 综合版画/2009
《囚-抽烟的人》 综合版画/200957 x 71 cm | ¥ 8,800
1.9 -
 《囚:未来佛》 铸铜/2017
《囚:未来佛》 铸铜/201741.5 x 64 x 42 cm | ¥ 180,000
1.9 -
 《连理》 铸铜/2016
《连理》 铸铜/201621.5 x 61.7 x 27.5 cm | ¥ 130,000
1.9 -
 《囚-攀登高峰的人之二》 布面丙烯/2016
《囚-攀登高峰的人之二》 布面丙烯/2016150 x 150 cm | ¥ 225,000
1.8